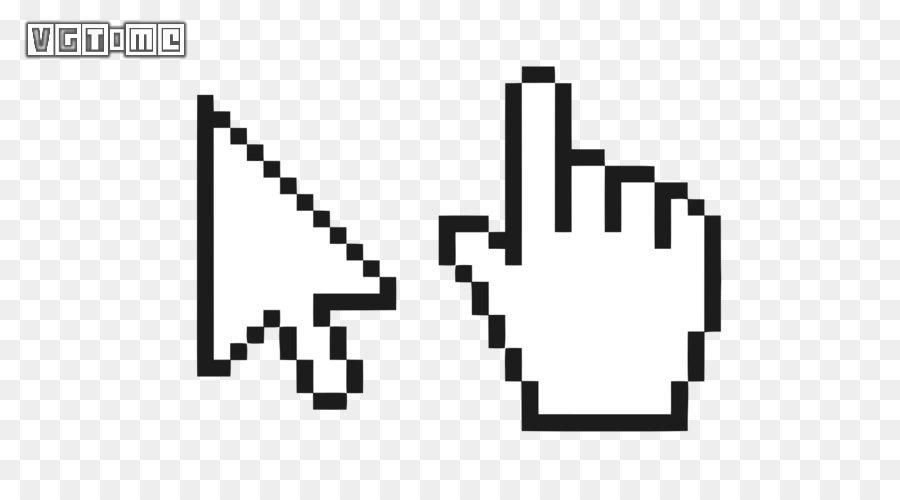简单的道理背后,是非常复杂和深奥的学术理论。
作为一个游戏玩家,每当游戏启动,拿起手柄,玩家就“成为”了游戏中的角色。这些角色在虚拟空间里能飞蟾走壁,上天遁地,能成为十恶不赦的大坏人,也能成为万人敬仰的英雄勇者。
现代电子游戏都希望能为玩家们提供更加沉浸的体验,希望玩家们拿起手柄之后就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虚拟世界的角色中,希望玩家们最终认为自己成为了屏幕里的他/她/它。
这个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也很好理解,但你知道如何从理论和学术上来解释它吗?
虚拟角色=鼠标?
当你开始游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曾经想过,究竟是什么令我们认为自己正处于游戏之中?是因为我们正在扮演马力欧脚上的鞋?究竟是怎样的东西,能令我们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柄有玩游戏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身处游戏中,根据游戏中角色的遭遇本能地作出反应呢?
在早期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将游戏角色与鼠标箭头挂起了钩。
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当玩家操纵马力欧或者是劳拉,在迷宫或者古墓中探险,这种程度的控制就如电脑的鼠标箭头一样。也就是说,早期研究学者倾向认为玩家在游戏中控制的其实是一个具有形象的箭头——因为两者在功能上是相似的,都具备一种“指哪打哪”的功能。
某些学者甚至认为玩家只是在驾驶/操控这些可操纵的游戏角色,而它们并不应该被认为有如同电影或者小说中的那种可以使得观看者代入的功能。
但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玩家并不应该因此感到自己身处在游戏世界中,毕竟只是控制一个类似鼠标箭头功能的东西在移动,这东西只是在完成玩家所提出的指令,这就使得游戏角色更像是一种处理任务的工具,而不是存在于游戏世界中的角色。
你可能会说,“这不可能啊!鼠标箭头和游戏人物完全两码事,根本不一样啊!”这点的确没错,鼠标箭头这种不需要投入感情的工具,怎么可能和游戏中在故事衬托下“有血有肉”的角色相比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玩家会觉得马力欧或者劳拉就是“我(即玩家)”在游戏世界中的化身,鼠标箭头无法提供同样的感觉,也无法提供这些游戏角色的特殊能力予以玩家使用。它甚至无法提供当这些角色即将死亡时,玩家所要承受的危机感。毕竟鼠标箭头是一种与游戏角色不同的存在,它无法像游戏角色一样,提供玩家“我”存在于游戏中的感觉。
这时候又出现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解释玩家延伸到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则是将虚拟角色理解成义体。
虚拟角色=义体?
如果我们能将义体理解为我们人类身体的一种延伸,那将虚拟的游戏角色理解成我们身体的延伸也挺合理的。
这个等式能够成立的基础在于,这一种义体式的代理(游戏角色),它的功能在于延伸或者成为玩家身体的义体,它是一种触觉的发动器或者动觉的连接,这种特性常见于动作、体育或者动作冒险类游戏角色之中。
通过实时控制中的“魔法”(注:游戏可以被理解成存在于“魔法圈”内的产物,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在“魔法圈”中均能合理化),玩家则可以通过这种义体直接接触游戏世界,就如一只延伸出来的手臂一般。而这种延伸的概念,则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自我存在的延伸(虚拟角色)游玩。
但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概念之中,义体式的游戏角色并不单纯只是玩家作为动作和感知物体的延伸,所以这种「玩家—虚拟角色」的关系本身又处于一个谬论之中。这个谬论即「玩家—虚拟角色」概念同时含有延伸和换位双重意义。
简单来说,按照延伸这个理论的话,玩家依然存在于现实世界,只是感知扩展到了游戏中;但同时玩家又认为自己正处于虚拟世界中,并且还能在其中自由行动,这相当于换位——我们不能在“这里”和“那里”同时出现,所以它又是矛盾的。
身体延伸的现象学
要解决延伸和换位同时存在于游戏角色体现中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代入体验的不同类型的现象学分析(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中寻找。而解决方法,或许是需要使用游戏角色的延伸来调和特定种类的关系,这是一种身体作为主观和身体作为客观之间的关系,也是身体空间以及外部空间之间的关系。
在现象学中,学者认为,主体并不是指一个拥有躯体的心灵,而是指心灵就是躯体本身。主体不是“我想(I Think)”,而是“我可以(I Can)”。只有通过这种“我可以“,我们才能感知世界。
例如在《GTA V》以及《超级马力欧奥德赛》中,只有当我们成为不同的“我可以”,我们就可以“穿”上另一个躯体的“鞋”,然后踏入另一个世界。
在有了上述的解释之后,我们的躯体将同时成为“主观”和“客观”,即是观看者(在物理空间的玩家)和被观看者(在虚拟空间的虚拟角色)是同一人。
在行动中,躯体本身是无形的,从体验中抽离,它可以通过科技或者工具将自己延伸。例如老年人所使用的拐杖,或者是《潜龙谍影V》中主角使用的假肢,甚至大部分人带着的眼镜,都是身体的延伸,因为我们的身体并不止于皮肤。
当我们完全适应了它们的存在,这些科技性的延伸也会如躯体本身一样被透明化。就好像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去做某些东西,因为我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我们并不会特别感知到手的存在,我们只会感受到物件的存在。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实际和潜在的可能性,以及情景的需求,都将定义我们躯体体验的“这里”和“那里”。
当完全适应之后,拐杖会成为自我的延伸
虚拟角色以及延伸的触感
现在,让我们回到延伸和虚拟角色的概念中。
在我们的日常游戏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游戏都需要玩家能熟练使用手柄,毕竟游戏角色是被玩家实时操控的,无论是摇杆、鼠标、滑轮、动作捕捉、或者任何其他种类的操作方式,玩家都需要去精通,甚至达到能够直觉式地使用手柄。
在通常的情况下,玩家将因此“转移”自己进入到游戏世界里,这种概念就好比我们学会演奏一种乐器或者是驾驶汽车。然而与演奏乐器和开车不同的是,游戏将延伸你的身体,穿越物理间隔,直接进入到屏幕里的虚拟空间。
然而当游戏需要我们使用虚拟角色来穿越物理间隔之后,又会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那就是究竟哪一种客体才是现在这一刻“插入”到我们身体的义肢呢?是手柄?是屏幕?还是在屏幕里边的虚拟角色?因为就如上边所说,当我们完全适应了它们的时候,这些科技性的延伸也会透明化。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80年代早期的静态背景游戏上寻找答案。
爵士乐钢琴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David Sudnow曾艰苦地记录自己如何在数百小时的训练后成为主机版《Breakout》的专家,他首先注意到某种“电子脐带式连接”,这种连接可以让我们的手与屏幕下方的可操纵方块进行连接。他表示,“那里和这里均存在着空间,我们用动作穿越被连接起来的空隙,而这一动作使得我们因此感觉到一种对事物的平衡延伸触摸。”
Breakout
Sudnow的言论直接地指出了实时操控游戏的核心——玩家觉得他们是处于一个延伸触摸的过程之中,而这种触摸使得他们能触摸到屏幕那一端的物件。作为玩家,我们跨越物理限制,穿越我们身体空间的“这里”,通过被连接起来的空隙,来到屏幕空间的“那里”。
需要注意的是,这时候的触摸体验并不是一种自我躯体的延伸,而是实际碰触到物理物件的体验。换一句话来说,这是种模拟的触摸,可以“成为”某一种物理碰触。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屏幕空间被给与了与物理现实本能代入类似的功能。
由上边所提到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在《Breakout》游戏中,下方出现那一块可被玩家操纵移动的方块,变成了一个义体人偶,它直接与玩家的手指挂钩。而这块出现在屏幕中的方块也变成了对于手柄的物理延伸的合理对照物。
而在经过了进一步的艰苦练习之后,Sudnow甚至意识到,不只是玩家可控制的那一块小方块,整个游戏或许都能转变成一个完整的义体,就如一个乐器一样。我们或许可以称这种用于经典街机动作游戏的游玩形式为演奏式游玩(instrument play),因为这和精通一种乐器演奏的方式类似。
需要在这里澄清一下的是,那个年代下的这种方式并不是指虚拟人物与环境的对立(注:虚拟角色还是存在的,但其本身会被最小化,如在《Breakout》中,虚拟人偶就变成了一块普通的、可被操纵移动的方块,它与环境融合,因此这种情况下,它们和环境的关系在这种类型中会变得模糊),而仅仅只是将手柄和屏幕都想象作一个器官,一种复合的机构。
虚拟人偶=扯线木偶
然而,上边所提到的这种演奏式游玩的模式,在以玩家控制虚拟游戏人偶行动而设计的卷轴式动作冒险游戏中就不太成立了。
在这种游戏中,外部的游戏空间、环境,以及一个可以让我们延伸我们躯体的虚拟游戏人偶存在的世界,这些东西都会清晰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游戏会让虚拟人偶和环境清晰地被区分开(这点就和上边所提到的《Breakout》不一样)。这些游戏,在游戏类型的发展从静态背景游戏(如《吃豆人》),向动态卷轴背景游戏(如《超级马力欧》)转变中渐渐出现。
尽管马力欧与《Breakout》的方块有相似之处,但在动作冒险游戏中,虚拟人偶之于其环境的关系被放大了。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当玩家控制马力欧头顶问号砖块(与场景互动)的时候,虚拟人偶才能因此获得金币(或蘑菇)。
我们在玩卷轴动作冒险类游戏时,并不能只是像玩静态背景游戏一样,因为这种游戏需要玩家能够像控制扯线木偶一样操纵游戏中提供的角色,并在游戏环境中感知和直觉地行动(例如操纵、探索以及战斗等等),在这里,游戏世界是外部的,自治的,也是未知的,它并非如静态背景游戏一般一目了然,它需要玩家对未知环境进行探索。
当然,这里其实也有另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中,游戏人物能让玩家不需要直接地对屏幕里边的游戏环境作出行动,而且也不会义体化。或者说,这类游戏本身就不是这样设计的。在这种游戏里边,游戏角色被象征性地控制,而不是直接地操纵它来互动,玩家给与角色命令,然后角色则会执行,《暗黑破坏神》和《模拟人生》均是使用这种象征性互动方式的代表游戏。
代理式体现
随着上边提到的,义体式游戏角色通过现象学的“躯体”,并将其双重本质延伸到屏幕空间中,这些屏幕里的扯线木偶因此成为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玩家“我可以”的一部分。
当我们使用熟悉手柄以及游戏操作,以此来控制游戏角色后,这个角色是我们身体的延伸,也使得屏幕空间变成我们主观存在的世界,这是一个我们栖息以及挣扎生存的地方,而这些游戏角色给与我们一个新的可视性,新的事物去感知,以及新可能性去延续我们的行动。
这时候,我们能说这个扯线木偶的关键功能是这样的:当它延伸躯体—主体和相应的躯体空间到屏幕空间,它将作用并作为我们客观身体的替身或者代替品,一个代表我们,并存在在游戏空间中的代理。而因为这种义体式游戏角色的存在,允许我们能执行一个主观和客观躯体的短暂分离,并穿越物理间隔。
这个时候,我们本身的身体将被“废弃”,因为当我们通过游戏角色进入屏幕空间后,我们存在于“那里”的身体,安全地坐在沙发/椅子上的现实身躯,将会被渲染成一个存在于客观空间中的不相关躯体。
临场感与镜头躯体
尽管扯线木偶式的游戏角色,其转移空间的方式可以作用于绝大部分2D卷轴背景游戏,然而并不代表它能满足我们现今普遍存在的沉浸式3D游戏世界,或者说,第一人称游戏。
尽管具备延伸性的2D游戏角色和那些扯线木偶的确能将我们的躯体转移到屏幕空间,而我们也可以将它们作为我们处于外部空间的身体,那个现在变成客观的躯体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这样就说这种义体式的木偶可以转移我们的肉体空间,这绝对是不合理的。就算这些木偶的确可以延伸并重塑它,它们也仅仅是被远程控制的代理,无法作用于第一人称游戏中的临场式代入感。
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考虑3D游戏世界中的代入呢?
我们应该这样想,在这种第一人称游戏中,我们并不是像之前2D卷轴游戏一样,操纵木偶,并使之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或许在这种游戏的形式下,我们并不是处于外部,而是“实在”地处于3D世界之中。
以镜头作为躯体的游戏角色体验,那些第一人称游戏经常出现的控制镜头=控制角色身体的方式,令它成为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游戏类型。游走于实时产生的3D环境,我们并非通过外部来感知环境,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存在与另一个空间。
第一人称游戏角色的镜头躯体,提供屏幕作为一种主要义体的连接,这种连接将作用为我们躯体移动和观看的延伸,并产生出一种通过游戏角色镜头—躯体的义体式运动视觉。
扯线木偶并不是自己移动的,而是通过躯体的帮助下被移动;与之相反的,镜头躯体不能通过身躯的帮助下被移动,它不能作为一个外部目标,因为我们不能像我们看自己双手一样,去直接观察我们的双眼。在运动游戏角色中,这里会有多一层需要熟练掌握的能力,那就是“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镜头控制。
这种镜头控制,将通过义体式游戏角色,来取代我们的视觉感知器官,并产生一种独特的义体式临场体验。举个例子,当我们玩《半条命2》的时候,玩家就是高登佛里曼,玩家将作为高登佛里曼感知周遭发生的一切。
结语
游戏,作为一种互动式媒体,它允许玩家操纵游戏中的角色/物件,并在虚拟的环境中漫游,而这种互动的形式,也让玩家有延伸自己进入另一个空间中的机会。
当我们开始游戏,那些可以直接被控制的游戏角色,例如马力欧或者劳拉,他们就像是赛车或者其他种类的可操纵的载具一样,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种义体式延伸,而他们也将躯体作为客观和主观的双重本质延伸到屏幕空间之中。
而在另一方面,在3D的游戏环境中,游戏角色的主要躯体,在现象学的层面中,它并不是可被控其身体的木偶,而是一个可操纵移动的虚拟镜头,而它也将在游戏过程中变成玩家移动视觉的一种延伸。
希望本文能作为一个引子,让更多的人了解关于自己是如何被延伸到屏幕另一边,并进一步理解游戏这种媒体的学术性。
*本文整理、节选并部分翻译自Rune Klevjer于2012年发表的文章《Enter the Avatar:The Phenomenology of Prosthetic Telepresence in Computer Games》,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的同学可以观看一下原文。
作者:神隐黑子
来源:vgtime
原地址:http://www.vgtime.com/topic/1058662.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