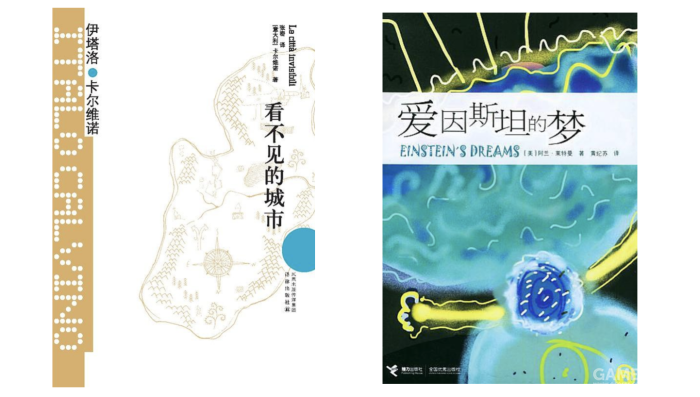“当我坐下来制作游戏时,我只想着做出最好的东西。”
此为 Jesper Juul 为其著作《
Handmade Pixels》所做的系列访谈之一,访谈时间为 2018-03-21,主题为独立游戏、文学及视觉风格等。原文请
点击此处。
考虑到整体篇幅,整个访谈将被拆分为上、下两篇。翻译如有错漏及未尽之处,还请批评指正。
Jesper:当别人问你的工作是什么时,你会如何介绍?
Jonathan:我经常编程,还做设计。往往我在编程上花更多时间,但是设计会引导所有编程工作。同时我也经营着一个游戏工作室,尽管我并不将这些作为人生目标(life goal)。有些人想搞一个公司。但我并不想成立公司,建立工作室不过是为了做有趣的事而采取的必要手段而已。因为如果你为别人的公司工作,你大概率不能做一个有创意的项目。
另外,我的工作室是一家自负盈亏的独立工作室。我们不接受发行商资助,因为发行商愿意投钱的项目往往在创意上不那么自由。
Jesper:你是否将自己描述为独立开发者?
Jonathan:我不知道。有些人将我视为某种独立开发者的典范,因为在2000年代初至中期,我一直在进行独立开发,并且当时独立(indie)的概念方兴未艾,而我的游戏《时空幻境》刚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我不喜欢那之后的所谓「独立共同体(indie community)」概念。《时空幻境》和其他一些游戏问世的 2008 年可真是个黄金时代。我认为2008年是从《N +》开始的。它虽然不及当年晚些发布的游戏,但也是相当成功。我想它大概卖了 7-10w 份,真的很不少了,而且还在 Xbox Live Arcade 上发售。这是个时代开始的信号,当然,那年晚些时候《时空幻境(Braid)》和《Castle Crasher》以及其他一些游戏就发售了。
2008 年发售的忍者横版过关游戏《N+》
当时的独立开发者的概念和当下似乎不同。我们是独立的人,我们做游戏,但我们并未将自己标榜为某个独立游戏社区的一员。那些标榜自己是独立开发者的人——把自己算做某个群体的成员——我觉得他们重点(priority)错了,起码跟我的重点有极大不同。
当我坐下来制作游戏时,我只想着做出最好的东西。无论是在想法方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我得确保我的执行力非常出色,毕竟所有想法都得靠技术实现。这意味着我得是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和时间规划者,我需要保证自己能高效工作。并且我需要确保我所做的事情对于我想要实现的更高愿景(Vision)非常重要。
我觉得自2010年以来建立的 「独立共同体」是基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一个特别好听的理由(good sounding philosophies),即任何人都可以制作游戏,人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他们的游戏表达自己。你能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而这个共同体对每个人都拍手欢迎。
这些都是积极的想法。但是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做游戏很难,制作一个出色的游戏真的非常非常难,因为做的时候必须时刻有“做最好的东西”的警觉(vigilance)。所以我并不怎么认为自己是这个「独立共同体」的一员。
Jesper:很有意思。独立开发相较于大型开发而言是一种更适合追求完美的方法,但是这和人人都可参与的 DIY 制作之间似乎有着矛盾。
Jonathan:确实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矛盾,特别是就最近几年在Twitter上的独立开发者而言。 DIY美学很棒,非商业美学很棒,无需考虑商业因素就可以创造性地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也很棒。但是,这是一个矛盾,有人在做这些事情之后又觉得自己有权利去要求商业上的成功。最近有很多抱怨:“我制作了自己的DIY非商业美学朋克游戏,但在 Steam上无人问津,所以整体游戏环境有问题”或“资本主义是坏的”。我认为这些牢骚都没意义。
我制作独立游戏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想自由地进行创作,能够不受众所周知的、遍及整个环境的商业规则约束。但这些商业规则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有效,它们能让玩家花钱去买游戏。
当你决定不参与其中时,其实你是在决定“很可能大部分人不会买我的游戏”。这是我做《时空幻境》的时候就有的觉悟。《时空幻境》是个在当时显得怪异的游戏。《见证者(The Witness)》更是一个机制上(mechanically)的怪胎,它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游戏机制可言,而且是个100 小时才能通关的游戏。
The Witness
Jesper:其实它也有它自己的游戏机制。
Jonathon:好吧,它可能有个听起来很无趣的机制。但我认为它比其他游戏精妙(subtle)得多。这些都是怪异的设计,当我们着手进行设计时,我就想:“是的,没人愿意玩这个。”但那就是我所做的选择。我觉得许多当前的独立开发者还不清楚,这是他们主动要做的选择。如果你决定做这个游戏,你就得有没人愿意买单的觉悟。而独立游戏就是这样的。
Jesper:这很有趣,我理解了。但与此同时,你也是最早谈论个人表达(personal perspective)和创新等价值的人之一,你也参与了实验性游戏工作坊(Experimental Gameplay Workshop,下称 EGW)的发起。EGW 的最初宣传纲领中说“电影和音乐有实验的空间,但是游戏却没有,而EGW就是希望为游戏提供一个实验室”。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强调个人表达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胜利(won)了?
Jonathan:某种意义上也许吧,但我不确定它已经赢了。你可以说强调个人表达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趋势。
当时我参与 EGW 的动因是,我发现我们每年举办会议,批判 3A游戏如何不够实验性以及它们如何执迷不悟。但每个人每年都这么批判,而大家没有啥实际动作。
那我们如何才能鼓励人们不再泛泛地抱怨?我们如何鼓励人们在现实中做更多新事情?而互联网上早已经有人在做有趣和疯狂事情,但他们从没听过我们的理论,而我们该如何向这些没有听过理论的人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呢?而且我们是否可以为“有趣和疯狂”提供孵化环境呢?
之所以称为“实验性游戏”,是因为你在实验某种明确(specific)的东西,而一个游戏里有没有这种东西你其实能明显感知到。这和“我只是想做一些和现存事物不同的东西,但没什么具体的想法”有所不同。
我觉得,如果你要发起一场促进更多创意的运动,那就得有衡量这个运动是否成功以及是否在前进的指标。那就是我当时加入 EGW 的想法,我认为(用游戏促进创新的)时机已经到了,因为制作游戏非常容易,已经有许多人在制作无人问津的小众游戏。
如今,有 Twitter 账号每天推 Steam 当天发售的游戏的预览。 其实很快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都很无趣,但是偶尔会有几个游戏很有趣。按百分比计来算,游戏中创新的比率可能是很小的,但游戏总体的数量却极大的增加了。这为什么能够发生?主要是游戏引擎工具的便捷和互联网使得制作和找到受众变得方便了。所以这并不意味着 EGW 赢了。
Jesper:我不是说EGW赢了,而是说这种实验性游戏的理念被大家接受了。
Jonathon:是的,这个理念胜利了。我们该庆幸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毫无创造力的虚无世界中。我认为通过举办 EGW (它现在还在运行),我们表达和传播了一些理念,而一些人也真正被这些理念所影响,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依然认为 EGW所做的只是造成这种历史趋势中的微小因素。
Jesper:你说过游戏设计师应该问问题。这也就是你所说的,在实验性游戏中要问出某个具体的问题(a concrete question)吗?
Jonathon:是的。
在 GDC 中举行的 EGW Presentation Session
Jesper:到目前为止,游戏制作听起来很像是一种按部就班的科学操作,那其是否有精神上的要求?
Jonathon:有的。EGW强调游戏是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像是建筑的艺术形式。因为建筑物必须能够站得住,而且必须能够被人使用以发挥其功能。虽然有着这些限制,建筑艺术仍然有很大的自由和表达能力,并且能够产生有趣的作品。
与之相对的是,诗歌非常自由,除了极个别的情境下,其几乎没有形式上的限制。而我发现很多人就像写诗一样在做无方向的创意(undirected creativity)。对我来说,随意的古怪想法并不如切实有效的想法好。
我在设计游戏时通常涉及一些基本的游戏公理,然后探索其不同形式的排列。《见证者》就是这么设计的。这些想法是在设计时完成的,而不是在编程的时候产生的。
Jesper:在《见证者》中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许多连线谜题的答案在环境以及一些事物在屏幕上的呈现方式中。在某种程度上,它似乎与我们通常的游戏方式相反,因为玩家不能仅仅盯着谜题,还得关注外在的环境,并且意识到它们是相关联的。
Jonathon:关于这一点我有很多想说的。我不会说游戏一开始就在误导玩家,但游戏确实只会将玩家的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事物上,玩家必须自己扩大注意力。这是该游戏希望带来的快乐之一,即玩家可以扩展自己正在关注的内容。当玩家意识到自己需要放宽注意点时,他们会感到惊喜。
我刚才所说的游戏设计使得游戏中存在一些机会,使得玩家能够意识到自己必须考虑更多。有时候,玩家会卡关,但卡关的原因是玩家主动忽视了很多环境中特别明显的要素。玩家往往预设了环境因素无关紧要,但当他们发现环境因素相关时,也就找到了谜题的答案。
做这样的设计是一种精巧的高难度操作,因为这需要通盘考虑所有的信息。游戏中有一两个谜题要求玩家必须从特定的角度对环境进行观察,但这几个观察点我也做了对应的指引。所以设计的原则还是使得事情尽量明显,虽然我知道这样还是会有很多玩家看不见。
这个游戏通过游戏形式制造惊喜,即“如何通过解谜游戏的谜底来表达信息,在这个简化的幻想世界中,如何穷尽所有要素的极致来传达信息。”游戏世界中有光、影和声音,游戏设计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些元素来表达一个连贯的概念,同时当这些游戏元素开始相互互动,事情很快就变得复杂。这也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制作游戏是很难的”的例证。
因为在你意识到之前,事物之前就在相互影响,而这正是现实的基本特征。举个例子,一个工程师在绘制图像时并不会考虑其正在使用的像素着色器(pixel shader)是对真实光影在某个角度反射的一个理想化模拟。此时图像其实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角度。而利用这一点,可以来制作有趣的谜题,这也被引入了我的游戏,也是我游戏的核心理念。我通过声音和色彩来提供一种观察角度。
The Witness:环境与谜题互动
Jesper:我认为这很有趣,这让我想到很多人批评现在的游戏过分注重优化(optimization)了。有人认为,当过分进行优化时,很多事物被模糊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见证者》是对“优化风潮”的批驳。
Jonathan:我从未从这个角度考虑过,但我想你说的是对的。有些人在被互联网的任何信息剧透之前获得了游戏的预发行版本,包括我认识的几个解谜游戏“专家”,他们通关了游戏但甚至都没找到了游戏的一半内容。
但我是故意这么设计的。如果你的视角太狭隘,你就看不到全部的东西。我不认为我刻意想“惩罚”那些持有特定观点的人,但游戏本身确实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Jesper:我在游戏中有时就被“惩罚”了,但我想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
Jonathan:这游戏有些部分很难。即使有的时候你以为了解了这款游戏,但实际上你还是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找谜底。就算你已经过了几个别有深意的关卡,自以为知道了游戏的门道,但当你进入了几个新的关卡,你依然不确定自己该把注意力放到哪里。有时候你当下被卡关了,你可以先离开,但你的潜意识依然会留心着这个关卡,然后再回来解。所以游戏中并没有一个通用的解谜套路。
Jesper:我想问问你和文学的关系。因为你很多次提到了文学。在《时空幻境》中,文学当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你提到了好几个作品和作家,而且整个关卡设计看来像是阿兰·莱特曼的《爱因斯坦的梦》。
Jonathan:这得回到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它像是《爱因斯坦的梦》的更早版本。每年我去游戏开发者大会,人们都在说要讲更好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故事模型都是动作电影。而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好故事,你得寻求一种不一样的模型。
对《时空幻境》而言,还有些不同。“我想用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来做我的关卡设计,或者做我的游戏机制”。但是就故事部分而言,其受到书籍的影响远大于电影。
我将之视为一本插图书。插图书中总是有文字有图片,我觉得玩法就等于书中的文字,而游戏中的文字就像是插图书中的图片。在一些场合,游戏中出现大段文字来提供一些新内容,但游戏性(gameplay)本身还是这个作品的主要内容。
Jesper:好的。这就好比线性叙事和跨时空叙事。动作电影总是非常注重因果性,如果 A 发生,那么必然导致 B 结果。而你所描述的是一个更少受到因果链影响的空间。
Jonathan:也许艺术形式也各有千秋吧,导致小说总是比电影好。但我也确实看过一些电影比小说还好的作品,比如说最开始并不想被拍成电影的 David Lynch 的《穆赫兰道》。当我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它在我脑海中构建了一个非线形的空间。我觉得这种非线形叙事肯定有办法实现,而电影不过是商业工业所选取的形式。但游戏中用的全是线形叙事,高预算的游戏用的是像《致命武器2》或类似的时髦模型。
Jesper:但现在流行的是像《X战警:天启》这样的电影或《特殊行动:一线生机》这样的游戏。
Jonathan:这游戏因为一些很基本的原因并不怎么吸引我。但确实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故事模型。
Jesper:你是想将游戏做成文学那样,还是只是从文学中借鉴一些东西?
Jonathan:我觉得这问题蛮滑稽。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一个读书多的人。因为我可能跟一般程序员相比阅读量还算可以,但跟生活中真正的阅读爱好者比我读得还是很少。有大量被视为经典的作品我都没读过。我读过一些好书,那些好书有很棒的故事。但这些好故事跟人们在游戏中试图讲的故事八杆子打不着。
所以我是否想把游戏做得跟文学似的呢?
直白的回答是:一点也不想。因为使得文学伟大的是文学本身。你可以做个在屏幕上读文本的游戏,但本质上那不过是一本有着垃圾 UI 的书。就这么做的话,游戏似乎能做文学能做的一切。但是这就违背了游戏的本质,那个让好的叙事发生的功能。“好的叙事对游戏很重要”这事学术圈已经讨论了多年,对于一些学者来说,问题在于如何让 AI 生产吸引玩家的故事。这就是游戏产业的《致命武器2》。
我也不知道前路在何方。因为游戏真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媒介。你看完电影后感叹 :“这真的是个很好的故事”和看完小说后说这句话时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一部电影呈现的好故事往往与摄影、表演以及众多小说中不存在的东西相关。其实我们总是在讨论“好”的时候不够具体。
游戏拥有的互动性使得游戏中的“好叙事”与小说和电影都不同。有的时候你甚至不能说那是一个故事。对于游戏来说,很多惯常用来塑造一个好故事的手法都需要被抛弃。人们对故事的反应并不会变化,但在游戏中从零开始发明讲故事的方法很难,而从书籍和电影中借鉴则是一条捷径。但捷径有时也是死胡同,而你也不得不将所有捷径上的进展清零以回到正道上。
Jesper:你选了一本不是情节驱动的书举例子,这很有趣。你曾经说你想为同样喜欢《万有引力之虹》的人做游戏。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你总希望使游戏更紧凑(tight),不好意思我一时找不到更恰切的词汇了,而托马斯·品钦似乎是个特别零散(sprawling)的作家,他的书里总是充满了段子、回忆和下流曲子。所以他在某个程度上影响你的游戏了吗?
Jonathan:这个话题上我也有不少想说的。先说说紧凑和零散吧。《时空幻境》是个特别紧凑的游戏,因为除了最后一个世界,其他的每个世界都遵循一样的结构:相同数量的拼图、解决一个问题去搞到拼图以及其他一些结构。
《见证者》在我看来就更零散。其中有超 600 个谜题,而且它们面向不同的主题。而且有些主题比其他几个更有趣。所以强制给这些主题设定一样数量的谜题是不对的。有些地方有 4 个谜题,有的地方有 37 个。就是这样。
所以《见证者》在这个意义上零散。但是在我们想表达特定想法的地方,我们往往设计地非常紧凑。我们可能跟《万有引力之虹》一样,在作品的中间加入了大量有趣的内容,但我们并没从任何意义上借鉴这本书的结构。
但是想法的密集程度、深度和精妙程度是我们必须仔细考量的。如今游戏中的想法总是很笨拙(ham-fisted),一点儿也不灵巧。跟《万有引力之虹》相比,很多人可能觉得《最后的生还者》有不错的剧情,但是前者中藏有的想法比后者多成千上万倍。正是由于《万有引力之虹》中的想法如此之多、如此之精妙,以至于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读者无法理解,但是你依然能捕捉到这些想法的吉光片羽。
在《见证者》中,我在这方面做了更多努力。我们在其中注入了很多想法,虽然玩家可能无法完全体会,这都没关系。我并不觉得我们能像一本书那样在游戏中容纳如此众多的点子,因为写作比编写和设计一个能运行的游戏简单太多了。但我不知道游戏是否永远都会在“想法密度”维度上落后。
另外《万有引力之虹》是在某个意义上非常自由的书。它不在意读者是否完全跟得上它的节奏。它提供自由和快乐,与此同时也包含很多阴暗的东西。我到目前还没见到哪个游戏能做到将两种相反的情绪同时呈现的。
Jesper: 《万有引力之虹》中如何转变声音、风格和语调这点非常有趣。似乎你的策略之一就是隐喻(allusion)和引用(citation)。你会引用一些在我看来是你精神导师的话。这在多大程度上是你游戏设计的一部分?比如说你在《时空幻境》中引用了《三位一体(Trinity)》:“那一刻便是永恒(On that moment hung eternity)”,在最后可以看到字幕中致谢了记者 William H. Lawrence,因为这句话其实是他说的。
Jonathan:我打包票很少人发现了这一点。
Jesper: 你觉得这是一个谜语吗?你是否将这也视为一个为玩家设计的追寻蛛丝马迹才能发现的挑战呢?
Jonathan: 有一点儿吧。在《时空幻境》中我确实这么做了,但《见证者》中的做法稍有不同。但下个游戏中我可能不会继续这么做,因为下个游戏可能和之前的游戏很不同。我在《时空幻境》中希望能够构建一个关于现实的隐喻,因为它是一个解谜游戏,而玩家就必须在其中找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意义。在《见证者》中我们做了大量的引用,而虽然游戏中没标明,但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些引用的出处。
做《时空幻境》时,我希望能表达的一个看法是,我对游戏的观点和很多人的观点有本质不同。扯远一点儿说,有些人说自己电影是因为电影让他们忘记生活中的痛苦,逃避现实。但这种逃避从不是我看电影的理由。我看电影是为了能进一步探索制作者所展示的一个想法。
《时空幻境》和《见证者》中有很多的想法,这俩游戏是做给对这些想法感兴趣的人的,而不是给那些想靠游戏逃避现实的人,毕竟玩一个这么硬核的解谜游戏怎么也算不上是逃避现实的好方法。
这两个作品并不是消遣工具,作品中所使用的大量引文将游戏和现实连接在一起,将你在玩这个游戏时的感受与不玩时的日常所思连接在一起。
(配图均来自互联网)
译者:The Ordinary
来源:机核
地址:https://www.gcores.com/articles/121769